村上春树的【暗杀骑士团长】,插图和评论。故事的男主是个36岁的画家。对肖像画有特殊才能。看到什么就能记住。不用照着模特儿画肖像。但是需要和模特儿谈话三次。以了解模特儿。他已经结婚七年。没有孩子。太太(名字叫做柚)在一家小建筑事务所工作。近来几个月没有和太太有过性交。一天太太说,她想离婚。自己已经和别人有了交往。这个交往中一定包括性交。画家同意离婚。搬出了自己的家。带的东西也很少。开着自己的二手小标志汽车,漫无目的地向北方开去。日本的北方实际上是东北方。这几年画家未曾有外遇。正常的夫妻生活,已经能满足他的欲望。但是一旦上路,外遇马上就来了。在一家路边的咖啡店,画家正坐着吃点心。近来一个女子,做到他面前。说自己被人跟踪了。还问画家她背后的人长得什么样。画家拿出常备的纸和笔,画出了背后桌上男人的模样。女人惊叹画家的画技。画家给女人买了一杯红茶和一块蛋糕。但是女人只吃了一口,喝了一口,就要和画家去旅馆。画家说他已经在火车站附近定了旅馆。女人说,那地方太差劲,房间和壁橱一样大。随即带他去了一家情人旅馆。有画家付了定金。女人并没有道谢。刚才的红茶和点心也没有道谢。进了旅馆之后,以下摘自原文:我在服务台预付一晚住宿费(她对此也同样没表现出感谢的意思),接过钥匙。一进房间她就先往浴缸放水,打开电视开关,细心调节照明。浴缸宽宽大大。确实比商务酒店舒心得多。看样子女子好像以前也来过几次这里——或类似这里的地方——她随即坐在床上脱对襟毛衣、脱白色衬衫、脱半身裙。长筒袜也拉了下来。她穿的是非常简素的白色内裤,也不很新,普通主妇去附近超市买东西穿的那种。手灵巧地绕到背部取下乳罩,叠好放在枕边。乳房不很大,也不特小。
“过来呀!”她对我说,“好不容易来这里一回,做个爱吧!”那是我在长时间旅行(或者流浪)过程中具有的唯一性体验。出乎意料的激战。她一共四次冲顶。可能难以置信,但哪一次都毫不含糊。我也射出两次。但不可思议的是,我这方面没有明显快感。和她交合时间里,我的脑袋似乎在考虑别的什么。“嗳,没准你好长时间没干这种事了?”她问我。“好几个月。”我老实回答。“知道的。”她说,“可那是为什么呢?你这人,看上去也不像没有女人缘啊……”“一言难尽。”“可怜,”说着,她温柔地抚摸我的脖子,“可怜!”可怜,我在脑袋里重复她的说法。给她一说,觉得自己真的成了可怜人。在陌生城镇莫名其妙的场所稀里糊涂地同名也不知道的女子有了肌肤之亲。做爱与做爱的间隙,两人喝了几瓶电冰箱里的啤酒。入睡想必已是后半夜一点了。第二天早上醒来时,哪里也不见她的姿影。检查一下裤袋里的钱夹。里面的东西原封不动。现钞也好信用卡也好借记卡也好驾驶证也好。我舒了口气。万一钱夹被拿走,马上走投无路。发生那种事的可能性也并非完全没有,得当心才是。引文完第二天早上画家醒来,女人已经走了,什么也没有拿走,什么也没有留下。画家又去了那家咖啡店吃早餐。看见了昨天女人说跟踪他的那个人,那人开着斯巴鲁汽车。那人看着画家。好像是说,没有实际说出:你小子干了什么我都知道。这对画家不知有什么刺激,记住了这个人的相貌,而且以后还画了他的像。评论:画家不画红衣女人,却画这个陌生人,说明画家对别人,特别是别的男人,对他的看法,很在意。2画家在同学的老宅里住下。这是一起学画画的同学,同学的父亲是著名画家羽田。但是同学没有继承画画的天赋。毕业后去了一家公司,已经是薪资丰厚的经理。他住在东京,父亲的老宅在山里。里面生活用具和画画用具一应俱全。画家本来不想再画别人委托的肖像画。虽然那是他唯一的挣钱的手段。他想画自己的作品。但是对着画布整天发呆,什么也画不出来。对面上山有一所大房子,里面住着一个50多岁的男子,叫做免色。一个奇怪的名字。头发全白。显然很有钱,他找画家给自己画肖像。酬金十分丰厚。让正缺钱的画家不能拒绝。虽然他再三声明自己不再画肖像了。这时画家找了个给业余班教绘画课的活计,虽然收入不多,也聊胜于无。绘画班上主要是家庭主妇。显然画家有些引诱力。他挑中了两个有孩子的主妇做情妇。是他挑女人,不是女人挑他,这时小说中特别说明的。他也没有多挑。主妇在日本叫做“人妻”。其中一个是富人的太太,年轻漂亮而且活泼,对性的要求很高而且奇特。就叫做小人妻。另外一个年纪较大,对性要求不高。但是很享受和画家的裸身聊天。可以叫做大人妻。这两个人妻利用画家独居的空房子。轮流到这里幽会。来了之后,首先要求做该做的事情,就是脱衣上床。然后在床上聊天。 两个人妻情妇的画家生活。画家有时候在做爱之后,给他们素描。人妻说,画得好极了。美丽而且淫荡。她们都很爱他。而且,好像她俩都知道对方和他的关系。是不是会交流,就不知道了。 素描那个年轻的人妻性欲比较强烈。有一次晚上打电话给画家,以下摘录:
“妙!下午早些可以的?”“当然可以。不过是星期六哟!”“总有办法可想。”“有什么事?”我问。“为什么问这个?”“因为这种时候你往这里打电话是很少有的事。”她从喉咙深处道出很小的声音,仿佛在微微调整呼吸。“这工夫一个人在车上呢,用手机打的。”“一个人在车上干什么?”“想一个人在车上,只一个人在车上。主妇嘛,偶尔是有这种时期的。不可以?”“不是不可以。一塌糊涂!”她叹息一声。就好像把东南西北的叹息集中起来压缩成的叹息。叹罢说道:“心想现在你在这里就好了。并且想从后面插进来多好!不要前戏什么的,湿透透的了,毫无问题。还要你肆无忌惮地来回搅动。”“够开心的。不过那么肆无忌惮地来回搅动,迷你车怕是有点儿小了。”“别贪心不足!”她说。“试试看!”
为什么问这个?”“因为这种时候你往这里打电话是很少有的事。”她从喉咙深处道出很小的声音,仿佛在微微调整呼吸。“这工夫一个人在车上呢,用手机打的。”“一个人在车上干什么?”“想一个人在车上,只一个人在车上。主妇嘛,偶尔是有这种时期的。不可以?”“不是不可以。一塌糊涂!”开车时的电话交媾,有树林子里野合的风味。她叹息一声。就好像把东南西北的叹息集中起来压缩成的叹息。叹罢说道:“心想现在你在这里就好了。并且想从后面插进来多好!不要前戏什么的,湿透透的了,毫无问题。还要你肆无忌惮地来回搅动。”“够开心的。不过那么肆无忌惮地来回搅动,迷你车怕是有点儿小了。”“别贪心不足!”她说。“试试看!”“用左手揉搓乳房,右手触摸阴蒂。”“右脚做什么好呢?车内音响倒好像能够调节。音乐放托尼·班奈特不碍事的?”“开哪家子玩笑!人家可是一本正经的。”“明白了。抱歉!那么就来正经的。”我说,“对了,现在你穿的是什么衣服?”“想知道我穿怎样的衣服?”她挑逗似的说。“想知道啊!我也好相应调整我的顺序嘛!”她在电话中把她身上的衣服详详细细说了一遍。成熟女性身上的衣服何等千变万化,这点每每让我惊讶。她用口头一件又一件依序脱下去。“怎样,足够硬了吧?”她问。“铁锤一般。”我说。“能钉钉子?”“那还用说!”世上有该钉钉子的铁锤,有该被铁锤钉的钉子——是谁说的来着?尼采?叔本华?也许这话谁也没说。我们通过电话线路,切切实实正正经经把身体缠在一起。以她为对象——或者此外任何人——做这种事是头一遭。可是一来她的语言描述相当细密和有刺激性,二来想象世界中实施的性行为,有的部分比实际肉体结合还要官能。语言有时极为直接,有时暗示以色情。如此一来二去,我竟至一泻而出。她也好像迎来高潮。我们好一会儿就那样一声不响地在电话两端调整呼吸。“那么,星期六下午见!”她清醒过来似的说,“关于那位免色君,也多少有话要说。” 边开边后入。3免色先生很满意画家给他画的肖像。邀请画家到他的宅邸吃晚饭。为此请了某饭店的厨师,和某酒吧的调酒师。费用一定不菲。免色请画家参观自己的车库,有四辆英国车。其中两辆捷豹。还有一辆小mini。在他的阳台上架着一台大型的双筒望远镜。面色说是北约的军用型号。画家试用,果真对面的房子里面都看得清清楚楚。免色说了他自己的故事。他之所以要搬到这个山里来。就是因为要观察对面那所房子。因为他认为那里的一个十三岁的女孩儿,是他的女儿。这个故事是这样的:大约十五年前,免色三十六七,和一位二十六七的流光溢彩的美貌女子交往。(以下把该女子成为光彩女)。虽然认真但是并不想结婚。所以打算如果对方想结婚,那就“二话不说地利利索索抽身退出”。二年多的时间关系很好,面色家里也有一整套她的衣服。在他二十九岁生日之后的一天,女友说要去他的办公室找他,以下是摘录:她坐在沙发上,蹭上身体。坐在免色的膝部,随机双手搂住他的身体接吻,那是舌头缠在一起的真正的深度接吻。长时间接吻之后,她伸手解开免色的裤带,摩挲他的那个物件。又掏出变硬的物件握在手里好一会儿。而后弯下身子,把它含在嘴里,让长长的舌尖环绕着缓缓爬移。舌头滑滑的热热的。这一连串行为让他诧异。因为事关性事,总的说来她始终是被动的。尤其在口交方面——无论被动还是主动——看上去她总是怀有不少抵触情绪。然而今天不知何故,她似乎积极主动寻求这一行为。到底发生什么了?他为之费解。
然后她霍地立起,甩开似的脱掉雅致的黑色无带浅口皮鞋,手伸到连衣裙下面麻利地拉下连裤袜,内裤也拉了下来。接着再次坐到他膝部,单手将他的物件导入自己体内。那里已带有充分湿度,简直就像活物一般滑润而自然地动了起来。一切都做得那么迅捷,迅捷得让他惊讶(总的说来,这也不像她。动作徐缓而温和是她的特点)。觉察到时,他已处于她的体内,柔软的壁褶整个把他包拢起来,沉静而又坚决地不断收紧。这和两人之间此前体验的任何性事都截然不同。温情、冷漠、坚硬、轻柔以及接受与拒绝似乎同时存在于此。他有如此不可思议的悖反性感触。但很难理解这具体意味什么。她骑在他上面,像驾驶小艇之人随波逐流那样急剧上下摇动肢体。披肩黑发如被强风吹拂的柳枝在空中曼舞。她开始失控,喘息声也逐渐加大。办公室门锁了还是没锁?免色没有把握。既觉得锁了,又觉得忘了。但现在不能起身查验。“不避孕可以的?”他问。事关避孕,平时她非常神经质。今天不用避孕。
光采女的追求者一定很多“不怕的,今天。”她在他耳边悄声低语。“你所担心的,一概没有。”她的所有表现都和平时不同。简直就像长眠于她体内的另一种人格突然醒来,把她的精神和肉体一并据为己有。他猜想今天对她大概是什么特殊日子。关于女性身体,男人不能理解的不知几多。她的动作越来越大胆和有力。除了不妨碍她的追求,他别无所能。不久,最后关头到来。他忍无可忍地一泻而出,她随之短暂发出异国小鸟般的叫声,子宫就像静等这一时刻一样将精液纳入底部,贪婪地吸取一尽。他得到的印象相当混沌,仿佛自己在黑暗中被莫名其妙的动物大口大口吞噬掉了。片刻,她像要把免色的身子推开一样欠身立起,不声不响地整理好连衣裙裙摆,将掉在地板上的连裤袜和内裤塞进手提包,拿着快步走去卫生间。很长时间都不从中出来。发生什么别的事了?正感到不安,她总算从卫生间出来了。此刻,无论衣着还是发型都一丝不乱,化妆也一如原来,嘴角挂着平日安谧的笑意。她轻吻一下免色的嘴唇,说好了得赶快走了,已经迟到了。说罢直接快步离去。看也没回头看一眼。步行离去的浅口皮鞋声仍声声留在他的耳底。那是最后一次见她。其后音讯杳然。他打去的电话也好寄去的信也好,概无回音。两个月后,她举行了婚礼。或者莫如说结婚消息他是后来从共同的熟人口中听得的。那位熟人为他未接到婚礼请柬甚至她结婚的事都被蒙在鼓里似乎感到相当意外。引文完在这次办公室做爱之后,光彩女友就和一个比她大十几岁的男人结了婚。这个男人很有钱,是大地主的儿子。自己是个地产商。免色偷窥的对面山上的那所房子,就是这个地产商的家。光彩女嫁给地产商之后,就搬到这里来。在结婚后7个月,光彩女友就生下一个女孩。按日子算,应该就是那次办公室做爱种下的种子。但是免色也不能肯定。因为有可能在那时候,光采女也和其他人做爱。但是免色特别说,光彩女在干完后在厕所里呆了很长时间。让他有点担心了。光采女出来之后马上就走了。老司机们会怀疑,光彩女在厕所里,把精液收集起来,如果这次受精失败,还可以利用收集到的精液。反复进行人工授精。这些事情让人觉得,光采女这次是专门来“收精”的。那就是坚决地要生免色的孩子。后来她嫁的是一个比她大十几岁的地产商。那人虽然已经年近五十却没有儿女。精子不中用的可能性很高。现代人工授精普及,老司机们在外面搞完之后,都很注意把自己的避孕套抓在手里,不给女方处理。虽然女方说是要扔掉。甚至拿来垃圾桶让你扔进去。老司机也不敢扔。谁知道她是不是拿上放进冰箱,等到男人一走,就去人工了。
在结婚几年之后,光采女就在这个山区散步的时候,被金环胡蜂蛰死了。她对胡蜂毒素十分敏感。随着年龄的增长,免色则有了一个执念。就是她生的女孩是自己的孩子。他花了重金,买了现在这所房子。这所房子之前有房主和住户。免色出的钱相比有点离谱,原住户才同意让出。他之所以要买这所房子,就是因为可以用高倍望远镜看对面房子的“女儿”。画家说,是不是应该找个机会,找到女孩的DNA查一查,确定女孩到底是不是自己的孩子?免色说不用了。画家理解。免色需要一个女儿。如果查出那孩子不是自己的,会让他更为失落。评论,故事从这里开始,有点像【伟大的盖茨比】了。只不过把恋人变成了女儿。免色对女儿执念,渐渐改变了画家的“理念”。在本书,所谓理念就是包括理想的观念。大约相当于人生观。画家当时的人生观,看重人生的自由和艺术创作。但是免色对女儿的执念,渐渐改变了画家的看法,变得认为生儿育女,建立家庭最为重要。免色的50多岁,他的现在应该类似于画家的未来。这让画家想到,自己到了50多岁,也会执着的把一个女孩当作自己女儿。但是却不能用行动关爱,也得不到对方的爱。那将是件多倒霉的事情。实际上,这对画家是个很现实的问题。他知道自己的太太也怀了孕。应该是在他俩还同居的时候怀上的。但是,前面说过,太太有几个月不和她性交了。而且现在正在和他办离婚手续。所以,这个孩子应该是别的男人的。但是,画家觉得,在那个孩子受孕的时段,他曾经和妻子“梦交”。要说梦交,老模板应该是牡丹亭中的杜丽娘。这部小说借用的东西可是不少。这个梦交非常真切,因为做完了梦,那东西还是湿湿的。以下是原文对这个梦的描述“那天天快亮的时候,我做了一个非常鲜明而淫秽的梦。梦中我在广尾公寓套间的一室。那是我和柚两人生活了六年的房间。有床。妻一个人睡在上面。我从天花板俯视她那样子,即我浮在空中。但没觉得多么不可思议。在梦中浮在空中对我是极为理所当然的事。决非不自然之举。而且无需说,我没以为是做梦。对于浮在空中的我来说,那无疑是此刻在此实际发生的事。为了不惊醒柚,我悄悄从天花板下来站在床尾。当时在性方面我十分兴奋。因为很长时间没抱她的身子了。我一点一点扒开她盖的被子。柚似乎睡得相当深沉(或者吃了安眠药也未可知),即使把被子整个扒掉,也没有醒的反应。身子一动不动。这使得我更加肆无忌惮。我慢慢花时间脱去她的睡裤,拉掉内裤。淡蓝色的睡衣,小小的白色棉质内裤。然而她还是没有睁眼醒来。不抵抗,不出声。
我温柔地分开她的腿,用手指触摸她的那个部位。那里暖暖裂开,已充分湿润,简直像在等待我触摸。我已经忍无可忍,将变硬的阳具探了进去。或者莫如说那个位置如温暖的奶油纳入我的阳具,积极吞噬进去。柚没有醒,但这时大口喘息起来,发出低微的声音,仿佛已急不可耐。手摸乳房,乳头如坚果一般硬挺。说不定她正在做一个深沉的梦,我想。可能在梦中把我错当成别的什么人了。这是因为,很长时间她都拒绝我的拥抱。但是,她做什么梦也好,梦中把我错当成谁也好,反正我都已经进入她的体内,这时不可能中止。倘若柚在这当中醒来得知对方是我,没准会受打击,气恼也说不定。果真如此,醒时再说就是。现在只能听之任之。我的脑袋在剧烈欲望的冲击下几乎处于决堤状态。起初,为了不把熟睡的柚弄醒,我避免过度刺激,静静地缓缓地抽动阳具。但不久自然而然地加快动作。因为她的肉壁明显欢迎我的到来,希求更粗暴些的动作。于是我很快迎来射精瞬间。本想久些留在她的那里,可是我再也无法控制自己。一来对我是久违的性交,二来她尽管在睡眠中,却做出迄今从未有过的积极反应。结果一泻而出,好几次反复不止。精液从她那里溢出,溢到外围流下,黏糊糊弄湿了床单。就算想中途停下,我也不知所措。以致我担心再这么倾泻下去,自己说不定直接沦为空壳。而柚却一不发出声音二不呼吸紊乱,只管昏昏沉睡。但另一方面,她的那里不肯放我出来——以坚定的意志急剧收缩不已,持续榨取我的体液。
这时我猛然醒来,察觉自己已实际射精。内裤被大量精液弄得一塌糊涂。我赶紧脱下以免弄脏床单,在卫生间洗了。然后走出房间,从后门进了院子里的温泉。那是个没有墙没有天花板的全开放露天浴池,走到之前冷得要命,而身体一旦沉入水中,往下简直暖到骨髓里去了。在黎明前万籁俱寂的时刻,我一个人泡在温泉里,一边听着冰为热气溶化而变成水滴一滴滴下落的声音,一边再三再四在脑海里再现梦中光景。由于记忆伴随的感触实在太真切了,无论如何都不能认为是梦。我确实去了广尾的公寓套间,确实同柚性交了。只能这样认为。我的双手还真真切切记得柚的肌肤那滑润的感触,我的阳具还留有她内侧的感触。那里强烈地需求我,紧紧钳住我不放(或许她把我误为别的什么人了,但反正那个对象是我)。柚的那里从周围牢牢裹住我的阳具,力图将我的精液一滴不剩地据为己有。
关于那个梦(或者类似梦的东西),某种愧疚感也不是没有。一言以蔽之,我在想像中强暴了妻。我剥去熟睡中的柚的衣服,没征得对方同意就插了进去。纵使夫妻之间,单方面的性交在法律上有时也是被视为暴力行为的。在这个意义上,我的行为决不是值得褒奖的行为。不过归根结底,客观看来那是梦。那是我的梦中体验。人们称之为梦。我并非刻意制造那场梦。我没有写那场梦的脚本。话虽这么说,那是我求之不得的行为这点也是事实。假如现实中——不是梦中——被置于那种状况,我恐怕还是如法炮制,可能还是悄悄剥去她的衣服擅自插入她的体内。我想抱柚的身子,想进入其中。我被这种强烈的欲望完全控制了。于是我在梦中以可能比现实夸张的形式付诸实施(反过来说,那是只能在梦中实现的事)。那活生生的性梦,一段时间给一个人持续孤独之旅的我带来某种幸福的实感,或者说是浮游感更合适?每当想起那场梦,我就觉得自己仍能作为一个生命同这个世界有机结合在一起,仍能通过肉感——不是理论不是观念——同这个世界密切相连。但与此同时,一想起恐怕某人——别处一个男人——以柚为对象实际受用那样的感觉,我的心就觉出针扎般的痛。那个人触摸她变硬的乳头、脱下她小小的白色内裤、将阳具插入她湿润的缝隙一再射精——每当想像那样的场景,自己心间就有流血般的痛切感。那是我有生以来(在能记得起来的限度内)初次产生的感觉。那是四月十九日天亮时分做的奇异的梦。于是我在日记中写下“昨夜,梦”,并在其下面用2B铅笔画了粗线。柚受孕正值这一时期。当然不能以针尖点中受胎时日。但说是那个时候也不值得奇怪。牡丹亭下,梦中也能怀孩子。
受孕就在这个时期。我想,这同免色所讲的十分相似。只是,免色是实际同肉身对象在办公室沙发上交合的,不是梦境。而恰在那时女方受孕了。之后马上同年长的资产家结婚,不久生了秋川真理惠。因此,免色认为秋川真理惠是自己的孩子自是有其根据的。可能性固然微乎其微,但作为现实并非不可能。而我呢,我同柚的一夜交合终归发生在梦中。那时我在青森县的山中,她在(大概)东京城中心。所以,柚即将生出的孩子不可能是我的。从逻辑上考虑,这点再清楚不过。
引文完画家和免色君一样有了“执念“,那就是他太太柚怀的孩子是他的。日本男性对”寝取“有特别爱好。很多动作片说的就是寝取。就是和睡着的女人性交。不过这个情节的老模板来自中国。西门庆干了睡着的潘金莲。这是大白天发生的,潘金莲赤身裸体,只带着兜肚,斜卧在席子上。西门庆悄没声地在她后面,把那东西插进去。等到潘金莲醒来,已经抽插数十次了。村上的描述显然更为梦境化了,所以柚即使冲顶几次也没有醒来。圣母玛丽亚也是在睡梦中受孕的。二,这个执念渐渐占据了画家的心理。原先那些自由啊,艺术啊,创作啊,都被压制了,或者说被杀死了。于是小说的名字也就出现了,那个骑士团长——是个画中的人物,变成了精灵,只有画家很看见。他自称自己是“理念“,也就是包括理想一些观念,其中有自由、艺术。都被对家庭和孩子的执念,杀死了。结果就是,画家询问太太柚,说自己还能不能回去。太太说可以,而且自己和男友的关系已经结束。原因是不想让那个男人,成为孩子的监护人。言外之意,这个监护人的空位,给画家留着了。至于那个孩子到底是谁的,她不说,画家也不想问。
画家的朋友告诉他,太太柚的男朋友,是个长得很漂亮的男人,画家和他一比,就很一般了。这样的男人,是很容易勾引人妻的。不过人妻,特别是有了孩子的人妻,有时候会“蓦然回首”,回到自己的家庭。实际上画家的两个人妻女友,其中一个也突然提出分手了,原因是“反正也不会有结果”。于是画家就回去了,和回头的太太重拾家庭生活,孩子生下来,是个女孩儿。画家很高兴啊。几年之后,画家每天接送孩子去幼儿园,路上经过一个小公园,和孩子一起玩耍。可惜的是这个街头公园太小了,没法比以前住的山林,画家相信孩子就是那次梦交的结果。并且坚定地认为,是不是也无所谓。就是在街上捡来的一个孩子,也一样会这样向她倾注父爱。画家自从回家,就要求肖像画经纪公司,给他找活计。给那些自恋董事长们画肖像。 这本是他讨厌的事儿,但是这是他唯一的收入来源。养家活口就靠这些钱了。而免色先生在找女儿方面也有进展。他心目中的女儿现在姓秋川,就叫她秋川小姐。她的母亲死了之后,由她的姑姑,就叫做秋川小姑,来照顾。秋川小姑三十多岁,没有结婚,长的相当漂亮,虽然比不上免色君的光采女,也是不错的。而且很有教养。免色君和秋川姑女二人第一次在画家家见面,就和小姑谈得很投机。小姑对免色君的捷豹汽车很感兴趣。说她父亲以前有一架,还到免色的捷豹中坐了一下。体验里面的内饰和气味。以后的两个人关系迅速发展。按画家的说法,有才又有财的男人,长得还很帅,很容易勾引女人的。13岁的秋川小姐也察觉到了这一点:小姑虽然说是要去图书馆当义工,但是打扮,首饰和衣服,都是会男友的规格。山中的秋川小姑在画家回归家庭之后几年,已经是高中生的秋川小姐打电话告诉他,她的胸部终于长大了。以前她曾担心自己的胸部长不大。而同学的胸部已经发育。另外,秋川小姑和免色君的关系,已经到了“随时可以结婚”的程度。但是还没有结婚。这让读者有点奇怪了,既然免色君对女儿有如此强烈的执念,那还不赶紧结婚,把姑女二人一起拉进家里?而对秋川小姐进行全方位的关爱。她的老爸早就加入了一个类似邪教的组织。给那个组织不停地送钱。以至于逐年卖掉收租的房产。而且经常不在家。所以如果秋川小姑嫁给了免色,那秋川小姐也会进驻免色家。但是免色迟迟没有结婚。说明免色君对自己的描述:他就是一个空壳。人生的内容的核心内容,是行为。没有行为的爱算不上什么了。面色君对物质——房子,车子,食物,有很多完整精密的行为。甚至安排了躲避地震的避难室。里面的食物、水,都按时更换。电器也按时充电。更不用说状态良好的四辆英国车,和整洁的大房子。但是对他心心念念的女儿的爱,却保留在心理层面,即使有机会也没能付诸行动。他很像“自恋的董事长“。把自己的画像挂在客厅里。也不能说免色君是个空壳了。他里面有很多对自己的爱的行为。秋川小姐和画家——她在绘画业余班的老师,关系有点特别。她一开就和画家老师说,担心自己的胸部太小。而且只有这两个人,能看到骑士团长的精灵。就是那个自称为理念的,画上的角色。他是精灵,只有60公分高。别人就不见,也听不见他说话。只有画家和秋川小姐看得见也听得见。按流行的分类,秋川小姐和画家是一族人。他们俩的感觉和心理相通。和别人无法交流。无所不知的团长精灵,在关键时刻,还分别对他们俩提出方向性指引。画家觉得秋川小姐很像他的妹妹,他妹妹在十三岁那年,因为先天性心脏病猝死。在小说中,为了让不知去向的秋川小姐安全回家,骑士团长引导画家到地狱中走了一圈,那是很不舒服的经历。这说明了,为了秋川小姐的安全,画家果断地付出他自己不曾估算的代价。
3说说那个【刺杀骑士团长】。这是一幅画的名字,。画的是歌剧唐璜的场面:唐璜勾引了骑士团长的女儿唐娜安娜。骑士团长找他决斗。年轻的唐璜一剑刺死了骑士团长。唐娜安娜看着,十分惊恐。这幅画是老画家雨田画的。放在他家的阁楼上。小说的主角画家,正好住进这所房子,在阁楼上发现了用纸包好的画。这时候老画家雨田已经90多岁,住在养老院里。据他儿子说,分不清歌剧和平底锅了。在莫扎特歌剧中,骑士团长的亡魂现身,邀请唐璜晚餐。天不怕地不怕的唐璜去了,被骑士团长直接拉进了地狱。另外,英国诗人拜伦也写过一首长诗唐璜。故事情节不同。并没有杀死骑士团长的情节。小说对这幅画的解释,认为该画来自雨田在二战时的经历。在1930年代,雨田在维也纳学油画,有一个奥地利女友。她的父亲的纳粹高官。他们和一些反纳粹的学生,组织了一次暗杀。目标就是女友的父亲,女友也参加了。事情失败了,雨田被捕,但是在日本外交部的干预下被驱逐出境,他的女友被杀。小说中的画家认为,这个骑士团长应该是雨田女友的父亲。虽然雨田学油画,这幅画却用了日本画的技法,画中人物穿的是日本古代服装。大致应该是这样:经过调查,画家还得知,雨田的弟弟,本在音乐学院学钢琴,被征兵参加侵华战争,在南京大屠杀中,长官逼迫他用刀砍杀中国人,因为不够坚决,被砍的人流着血挣扎,必须多砍几刀才死。两年后回到日本家乡,自杀了。总之这幅画画于残酷悲惨的时代,有残酷悲惨的故事。应该留作下回分解了。
喜欢老冠朋友的这个帖子的话,👍 请点这里投票,"赞" 助支持!
老冠 已标注本帖为原创内容,若需转载授权请联系网友本人。如果内容违规或侵权,请告知我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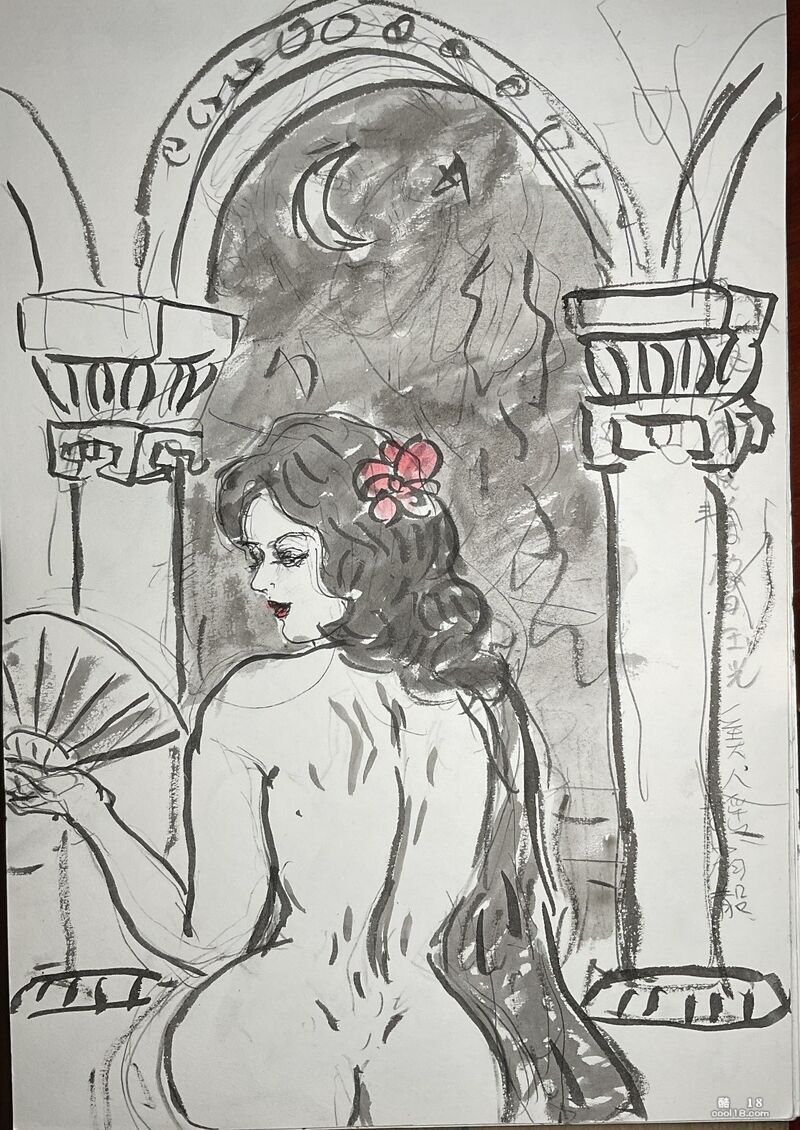


打开微信,扫一扫[Scan QR Code]
进入内容页点击屏幕右上分享按钮
楼主本月热帖推荐:
>>>查看更多帖主社区动态...